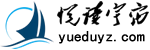大雪前,乡下的亲戚给我家背来了半编织袋他自己种的红薯。
亲戚离开后,我把那浑圆、饱满、粉嘟嘟的红薯晾晒于阳台一角,尔后就没上心当回事。时光匆匆,两个星期一晃而过,居然一直未碰它。
假日,颇爱下厨的我自告奋勇,围裙一系,从容上阵。煮饭前,我从红薯堆里信手捡了个红薯,去根,洗净,削掉皮,对开切成四瓣,放进电饭煲里的米上烀(烀,意为半蒸半煮,把食物弄熟)。
揭开饭锅盛饭时,黄橙橙的红薯香气随着袅袅蒸汽吸入鼻翼,人倏地为之一振。
那是熟稔的气息,那是久违的滋味。
细嚼慢品着酥软甜糯又香气扑鼻的红薯,往昔旧事不禁浮现出来。
我小时候,家里常吃红薯,每年几乎从深秋开始吃起,一整个冬季都不会停歇,甚至还要延续吃至开春。物质匮乏的年代,什么都需凭证凭票,计划供应的那点口粮,简直是杯水车薪,根本不够吃。活人岂能被尿憋死,于是,用红薯来弥补主食的不足。家乡宜兴西南是丘陵山区,如同个偌大的天然宝库,种什么长什么,肥沃的山丘上、田埂边、沟渠旁,乃至家前屋后的空地里,到处都栽满了一垄垄、一畦畦绿叶婆娑的红薯。霜降过后,熟透的红薯纷纷滚上了餐桌,滚进了我们的肚子。山农们红薯种得多,自己吃不了,多余的就拿到集市上出售。像我们这种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城镇老居民,没地可种,自然只能花钱买了吃。
那时家里是用土灶头烧饭做菜,烧的是硬柴禾。秋冬时节,父母亲总习惯在做饭前,准备好几个红薯,去根须,清洗干净,小的就整个儿,大的则剖开,放到饭锅内烀了给我们吃。偶尔也会在饭烧得将熟时,在灶膛的余火内埋入数个中等的红薯,待火熄灭时,红薯也烀熟了。这样烀出来的红薯表皮微焦,香气诱人,糖汁外溢,肉甚酥甜,我们姊妹几个常争先恐后地抢着吃。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我读小学三年级。那年的冬天似乎特别寒冷,傍晚放学时,天空飘起了棉絮般的雪花,行走在呼啸的朔风里,我冻得瑟瑟发抖,手脚都有些麻疼。母亲见我缩着脖要美文网子回家时头发上、肩膀上沾满了积雪,好不心疼,取过我背着的书包,便为我拍掸雪花。尔后,母亲轻盈一转身,从饭锅内拿给我一个热乎乎的烀红薯,我捧在手掌里捂着,还贴到脸颊上滚了几下,好久都舍不得吃,心里感到分外的暖和与幸福。
五年后,我已是一名有模有样的初二学生,说话像野鸭叫,饭量陡增。那时,我们每年都得去广阔的天地接受大自然的洗礼。
暮秋时节,柿子火红,稻谷金黄,满眼丰收景象。按分工,我们那天的任务是割稻。尽管稚嫩的手从未握过镰刀,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,弓背弯腰,摆开架势,挥镰收割。几个回合下来,我顿感喉冒青烟,眼闪金星,浑身乏力。原本就缺乏营养,还需孩子干大人活,如何能吃得消?很快,虚脱的我瘫坐在稻田里,近乎晕厥。班主任赵老师见状,如阵风一样奔了过来,一把将我揽在怀里,取出军用水壶,喂我喝水。稍顷,赵老师见我慢慢恢复了神志,从随身携带的军用书包里掏出一个烀红薯,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我说,你是饿成这样的,赶紧吃了。我接过那个温热的红薯,两行液体不禁从眼眶中奔泻而出。
旧时光已演绎成斑驳历史,新时代正向昂首阔步走来。而今的我们,早已不用为生存而担忧,因温饱而发愁,红薯也渐逐被其他食物所取代,慢慢淡出了我们的视野。偶尔想吃时,或去超市购上几斤,或到路边的烤红薯摊买一二个解馋。但我依然想吃烀红薯,因为它曾伴我度过了艰难困苦的岁月,我的血脉里流淌着红薯的成分,心里始终保存着对红薯的那份特殊情愫。